
2024-10-14 09:12 点击次数:173
提到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无疑是绕不过的名字。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努斯鲍姆并不陌生。如今77岁的她已经创作、编撰了50多本书,累计获得了60多个荣誉学位。其声誉之隆,即使放在整个学科发展脉络中都屈指可数,而这些足以让每个试图走进哲学领域更深处的读者,在许多个可能的时刻里频频与之照面。
不同于传统哲学研究者的古板玄虚,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努斯鲍姆时常衣着时尚,她爱做美甲、对超短裙情有独钟;就连在哲学写作上,她也在不断冲淡文学与哲学的边界,身体力行地抨击情感与理智的对立。爱与脆弱,一直是贯穿她研究生涯的核心脉络。从里到外,努斯鲍姆的存在本身就在持续冲刷着公众对哲学面貌的既有认知。
而在这样的深度与多维之下,努斯鲍姆本人几乎很少在中文世界露面。或者说,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那个处在学术之外、生活之中的她。一个在观念层面频繁谈论爱与脆弱的人,究竟会在真实生活中如何理解与践行它?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夏通过邮件第一次与努斯鲍姆取得了联系。邮件中,她对来自中文世界读者的关注表达了感谢,并主动询问这次采访是否可以主要围绕她年初译介至中文的新书《为动物的正义》展开,“由于女儿的离世,如今我生命中最大的事就是想推介她关于动物保护的工作”。这是努斯鲍姆近年的新作,也是一次母女合作的成果。她放弃了此前个人化的研究范式,尝试了一次全程与“关系”深度嵌入的写作,与女儿一起将先前的“能力论”扩展至包括动物在内,所有生命实现“繁兴生活”的终极愿景。
这条路诚然任务艰巨,但在努斯鲍姆看来,“我们不会因为还没能成功让所有人都繁衍生息,就因此放弃对整体人类福祉的追求。”
采写|申璐
以动物为媒,努斯鲍姆晚年的这次研究“转向”意味深长。
在文字往来中,每当谈到动物,昔日书中那个逻辑严谨的她总是忍不住打出感叹号。她激动地分享亲眼看到鲸鱼时的经历——“这里一片鳍,那里一条尾巴”,她称那次转瞬即逝的相遇像极了“瞥见所爱之人”的那个瞬间。所有有幸得见那样瞬间的人,一定会更真实地感觉到“这样的美好值得持存”,这是当我们谈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时,最深处的那个信念所在。它甚至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撑与辩论,只是因为,“太美好了”。
从动物伦理出发,我们也谈到了相关的争议。不少声音觉得她的观点太过理想化,与其说是“理论”,更接近于某种“信仰”。采访中,努斯鲍姆首度回应了这样的质疑,她直白说那并不只是“信仰”,如果需要,那是她完全可以“捍卫的东西”。但出于尊重,她没有将这些纳入她的政治观点。在她看来,“避免将我们相信的、且能用论据为之辩护的许多事情带入政治领域——我们就能按照一套政治原则共同生活”。
尽管以女性学者身份踏足这一领域,但努斯鲍姆对部分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另一条”动物保护路径不置可否,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对虐待动物一事负有责任。谈及外界将其与波伏瓦、阿伦特等女性学者相提并论,她也直言“这样的比较没什么意义”。在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走来之后,如今的努斯鲍姆在有意识与之保持审慎的距离。
言语之间,一个更侧重于行动而非言说的努斯鲍姆令人印象深刻。
采访最后,努斯鲍姆坦诚分享了她仍然计划想做的事,那些未竟的研究议题和尚未走完的路。如今77岁的她早已没有什么遗憾,仍然对生命本身——任何生命形式,抱有原初的爱与热情。她的研究正在与她的生活相融,且那团火并没有随着变老减损分毫。
下文为新京报记者与努斯鲍姆的邮件对话。

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1947—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道德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恩斯特·弗罗因德杰出贡献教授。作为美国当代最杰出、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她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力。曾被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与英国《展望》杂志列入“世界百名杰出知识分子”榜单。2003年获评英国《新政治家》杂志“我们时代的十二位伟大思想家”之一。2012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社会科学奖。2016年获京都奖·艺术与哲学奖,这个奖项尤其肯定“她发展了一套提倡可行性能力进路的新的正义理论”。2018年获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2021年获霍尔贝格奖。代表作有《善的脆弱性》《爱的知识》《欲望的治疗》《诗性正义》《女性与人类发展》《正义的前沿》《功利教育批判》《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政治情感》《愤怒与宽恕》《傲慢的堡垒》等,均有中文版问世。
是母女,也是学术盟友:
“我负责哲学,她提供法律”
新京报:你的研究横跨哲学、文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涉及到的具体议题囊括政治自由主义、刑法中的情感因素、性骚扰等不同类别。后来为什么转向了对动物权利的关注?你在《为动物的正义》中提到,这似乎和你的女儿有关?
玛莎·C.努斯鲍姆(下称努斯鲍姆):我其实很早就对动物权利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并在2006年出版《正义的前沿》时,就已经在书中简要描绘了我对这个议题的研究思路。但的确,我的女儿蕾切尔激励我做了更多的工作。她是一名律师,曾在一个关注动物权利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她的奉献精神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令人感动,也让我对动物本身以及它们在这个世界上遭遇的诸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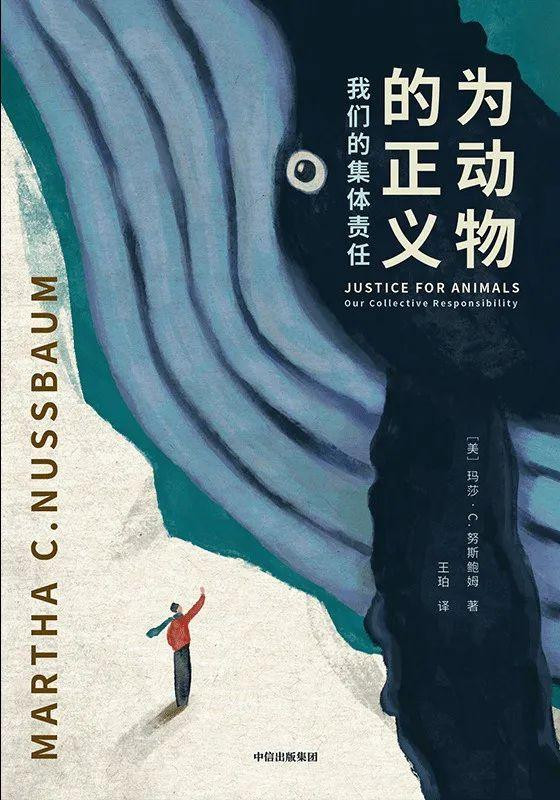
《为动物的正义》,作者: [美] 玛莎·C.努斯鲍姆 / 玛莎·努斯鲍姆,译者: 王珀,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4月。
新京报:你在《为动物的正义》的序言中提到,你和女儿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合作。“我们合作了一系列文章,我负责哲学,她提供法律”。这听起来很温暖,也很鼓舞。
努斯鲍姆:是的,如你所说,我们曾一起写了很多文章,并在人类发展与能力协会的会议上发表。她提供法律,我提供哲学,当年我们一起做这件事的时候真的很开心。除了是母女,我和她也是很好的伙伴。
就动物保护这个议题而言,我们的任务其实非常艰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去尝试解决。我们不会因为还没能成功让所有人都繁衍生息,就因此放弃对整体人类福祉的追求。在这方面,我认为法律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盟友——法律告诉我们什么是绝对必须要做的,并常常将其他目标定义为理想的或者说更遥远的愿景。而我的哲学理论则提供了一部“虚拟宪法”(virtual constitution),明晰了生物的权利。但是,我们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更明确的法律,来规定哪些行为是绝对非法的。如果种群和栖息地管理得当,我们没有理由不创造一个每种动物都有机会繁衍生息的世界。
但非常不幸的是,2019年,蕾切尔在成功完成一次器官移植手术后,却死于术后抗药性真菌感染。那时,她其实已经知道我在写一本关于动物正义的书,她甚至还读过其中一些章节草稿。从各种意义而言,她的去世对我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我计划将来写一本关于悲伤和哀悼的书,并在那本书中向世人讲述更多关于她的故事)。但我想我能做的可能就是将她的承诺发扬光大,并通过尽可能地完成好这本书,让书中的发现能够最终影响到这个世界。我所在的法学院还专门设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资助那些有志于从事动物权利保护事业的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法学院的三年学习。

玛莎·C.努斯鲍姆。图源: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网站。
不存在女性主义的“动物保护路径”,
这是我们的集体责任
新京报:在《为动物的正义》中,你将先前你所推崇的能力论进一步延伸到动物保护领域,并强调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核心权利清单。可否展开谈谈,能力论与传统动物伦理学中的主流论证方式有哪些不同?
努斯鲍姆:在这本书中,我选择了该领域三种最有影响力的论证方法,并呈现了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进一步论证了我的“能力论”为何是更胜一筹的。首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我称之为“如此像我们人类”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动物按照线性等级排列,并给予那些看起来和我们最像的动物以特权。我觉得这一理论不太符合自然规律:不同物种的能力各不相同,有些物种甚至拥有我们所缺乏的感知能力,比如感知磁场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认为之所以要善待(某些)动物,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它们。
之后,我又论证了“功利主义方法”,也就是边沁、彼得·辛格等人推崇的。这一理论侧重于痛苦本身,因此要好得多。但问题是,它把这个世界过于扁平化了。动物确实需要免受痛苦,但它们也需要社会交往、自由行动、以及享受特色的活动。我们应该把动物当作行动主体(agent),而不是各种需求满足的容器。
最后,我研究了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的“康德式路径”。从很多角度而言,我很欣赏这种路径,但同时也有些不同意见,这套路径认为动物只是“被动的公民”(passive citizens),也不是能动主体(agent)。在上述基础之上,我阐释并捍卫我的“能力论”。
新京报:你关注的是“有知觉的动物”(sentient animals),即那些对世界有主观视角、并能感受到痛苦和快乐的动物。当我们谈论动物保护时,为什么要强调动物的“知觉”?
努斯鲍姆:在我看来,有知觉是成为正义理论主体的必要条件。能够感受到疼痛、能够从自己的角度体验世界的生物,本质上与那些无活动能力的(inert)生物是不同的——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情都与它们有关,且对它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新京报:近年来,动物伦理学领域逐渐兴起一种新的“路径”。部分女性主义者试图在女性主义和动物保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结——女性和动物所受到的迫害,有相同的父权思想背景。在这一关联下,该脉络认为主流伦理观点只重视理性、通则,所反映的其实是男性的道德意识;而女性主义可以走“另一条路”,从特属于女性的道德经验出发,重视动物遭遇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情绪反应。我很好奇,作为长期关注动物伦理的女性学者,你会怎么看妇女解放和动物解放之间的关联?
努斯鲍姆:在我看来,这两条路径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情感(Emotion)本身就体现了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并不仅仅是女人的事情: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今天的不少生物学家也是如此。去年去世的一位杰出学者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也写了一本关于动物情感价值的精彩遗著。
的确有观点认为,人们需要重视动物在人类心理引起的情绪、情感反应。但这种观点其实是将情感与理智对立起来。而在我过往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抨击这种对立。情感(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情感)不是无意识的感觉,它们体现了人们对“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的思考。它们就是这样进化而来的,并持续引导我们朝着自己珍视的方向不断前进。
至于妇女解放和动物解放这点,我始终认为,人类女性和人类男性一样,都对虐待动物负有责任。因此,我们都需要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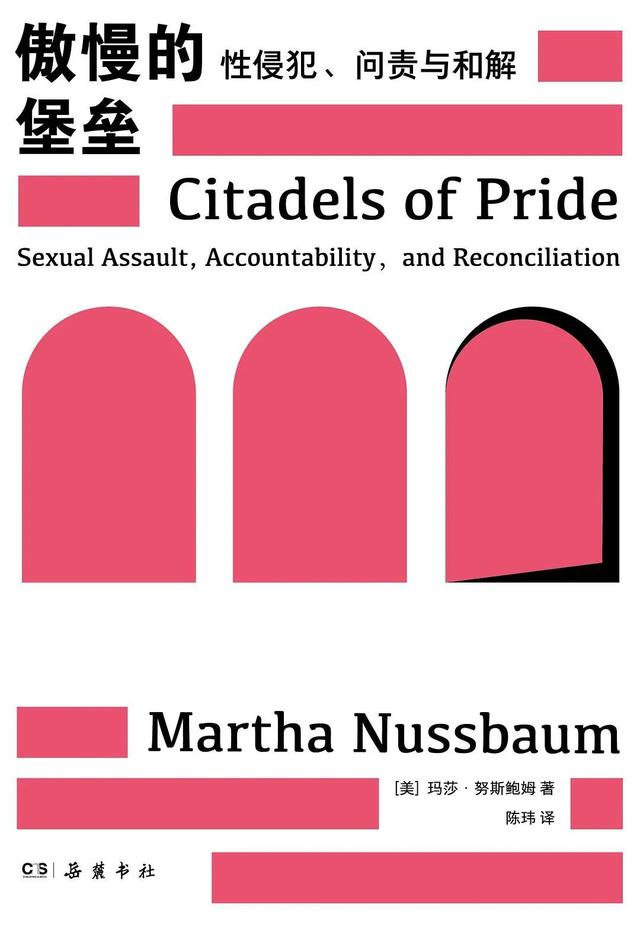
《傲慢的堡垒》作者:(美)玛莎·努斯鲍姆,译者:陈玮,浦睿文化丨岳麓书社2023年7月。
新京报:你在书中讲述曾在澳大利亚看到鲸鱼的经历。当时给你怎样的冲击?
努斯鲍姆:真正看到鲸鱼时,会让人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非常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经验——这里一片鳍,那里一条尾巴——就像亚里士多德描述的瞥见你所爱之人的那个瞬间一样。这是一种伴随着激动与惊奇的生命体验。我当时真切觉得——这是无比珍贵的,应该被保护和持存。
新京报:动物伦理学与传统的哲学讨论还有一定差异。你曾表示:“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价值——但同时要补充,这是在伦理上,尽管在我的政治理论中并不存在。”你声称,这只是你的个人信仰,与理论无关。对此,有评论认为你的整套动物保护理论有很浓厚的道德现实主义色彩,对此,你怎么看?以及研究者的个人信念和理论构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努斯鲍姆:长期以来,我一直在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观点辩护。根据这个观点看,社会在选择政治准则时,应当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即尊重我们在任何现代社会都能找到的、合理的、多元化的不同综合伦理、宗教和形而上观点。
如何表示这种“尊重”?就是要避免将政治准则建立在任何宗教或世俗的综合学说之上。这意味着政治准则必须是“狭窄的”(narrow)——不涵盖综合学说涉及的每一个生活领域,也是“单薄的”(thin)——用一种人人都能共享的伦理语言来表达,而不是用有争议的、形而上学或其他综合学说来表达。
这样做的目的是,政治准则将成为罗尔斯所说的“模块”,每个人都可以将其附加在自己的综合学说中。尽管我们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但我们都将共享这一模块。
和其他学者一样,我也有自己的综合学说。动物生命的内在价值只是这个学说的一部分。这不是“个人信仰”,而是我可以捍卫的东西。不过,出于对同胞的尊重,我并没有把我的这部分想法纳入政治观点中。
通情达理的人(指愿意在公平的合作条件下与他人共处的人)包括现实主义者和反现实主义者,也包括认识论基础主义者、整体主义者甚至怀疑论者,正如他们还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道教徒和无神论者一样。如果我们奉行罗尔斯所说的“回避”方法——即避免将我们相信的、且能用论据为之辩护的许多事情带入政治领域——我们就能按照一套政治原则共同生活。

纪录片《鲸的秘密》剧照。
站在77岁回望:
长寿的秘诀在于爱他人
新京报:你在很多作品中,都直言不讳地赞美面对脆弱和袒露脆弱的能力,并表示一个真正的良善社会是所有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脆弱、以及对他人的需要的社会。为什么你会如此执着且坚定地关注“脆弱性”这个主题?
努斯鲍姆:因为这的的确确就是事实。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完整的,是脆弱的,但哲学并不总是正视这一事实。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很少有关于情感的哲学著作,我们也很少有关于悲伤和哀悼的作品,更不用说关于生命周期——童年和衰老——的研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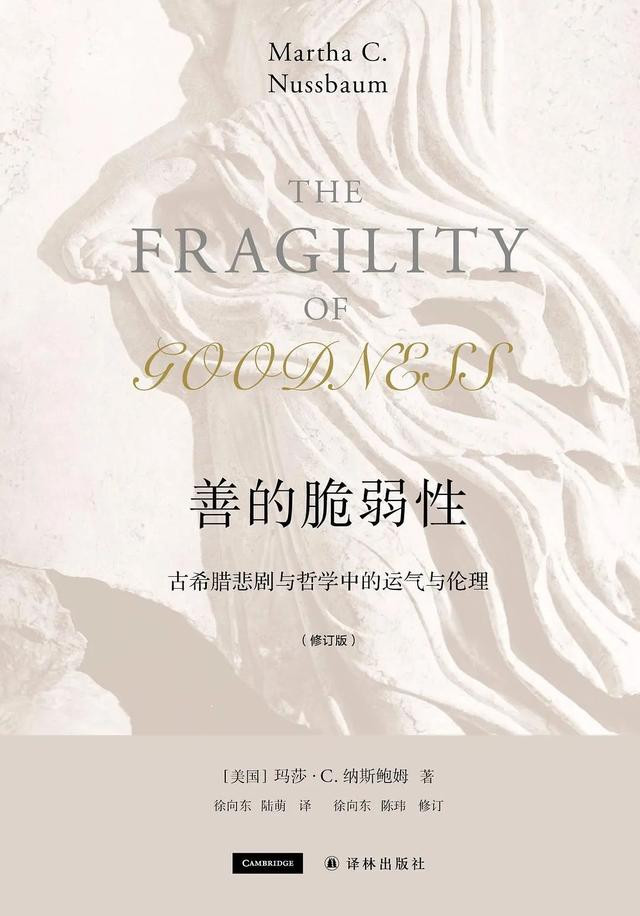
《善的脆弱性》,作者: [美] 玛莎·C.努斯鲍姆,译者: 徐向东 等,译林出版社 2018年9月。
新京报:这些是你如今最关心的几个议题吗?
努斯鲍姆:是的。我已经写完了一本和之前非常不同的书,将于今年11月正式出版。那本书暂定叫《沉默心灵的温柔:本杰明·布里顿和他的战争安魂曲》(暂译,THE TENDERNESS OF SILENT MINDS: BENJAMIN BRITTEN AND HIS WAR REQUIEM)。我这一生都热爱音乐,相信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战争、和平、爱与和解。通过与杰出的作曲家布里顿深入交流,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思考。
另外,我还在写一本关于歌剧及其与政治思想关系的长篇作品。这本书计划明年3月出版,书名暂定《爱的共和国:歌剧、呼吸与自由》(暂译,THE REPUBLIC OF LOVE: OPERA, BREATH, AND FREEDOM)。现在我马上要写的一章是关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歌剧《尼克松在中国》(NIXON IN CHINA)。我很好奇,中国的读者们对这部歌剧有怎样的理解和看法。对我而言,这是一部呼吁跨文化理解的美妙音乐作品。
回到之前聊到的动物保护这块,这些年我一直在为《纽约书评》撰写一些特定主题的评论文章,一篇是关于鲸鱼和我们如何阻碍其繁衍的多种方式,一篇是关于工厂化养殖业,还有一篇是关于保护动物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于获得了巴尔赞奖(Balzan Prize),我还打算组织一次会议,并编一本新书,到时将有一批年轻学者撰写一系列关于能力论和动物权利的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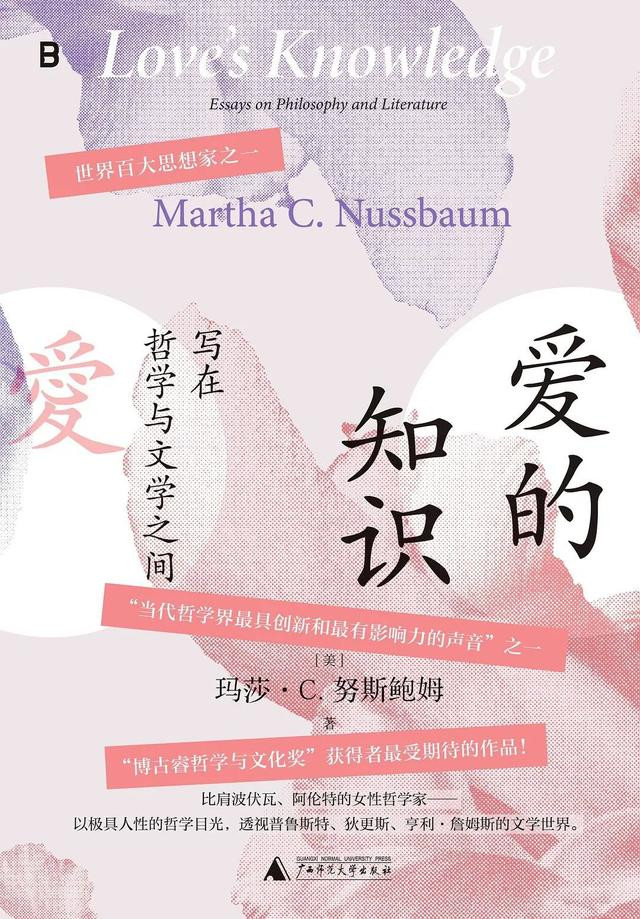
《爱的知识》,作者: 努斯鲍姆,译者: 李怡霖 等,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新京报:这些听上去都很令人期待,你似乎还有着蓬勃的创作动力。其实自进入公众视野以来,你已经出版了20多部作品,发表了500多篇文章,并获得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学术奖项。外媒有一些声音,将你比作“可与波伏瓦和阿伦特媲美的女哲学家”。你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努斯鲍姆:我认为将我和这两位女性相提并论没有多大的意义。她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和其他女哲学家相提并论,因为我并不认为存在一种独特的、只属于女性的哲学研究进路。如果非要比较,我更愿意与我的老师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并列,作为哲学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这种比较还算有意义。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20世纪重要的道德哲学家,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于1970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院士,次年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院士,并在1999年因其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主要研究为伦理学、知识论、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以及对道德和道德要求的本质的探究,一度主导了西方伦理理论的思维。主要著作包括《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羞耻与必然性》《道德运气》《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真理与真诚》等。
新京报:在77岁回望,可否与中国读者分享一些你如今的感受?
努斯鲍姆:在学术领域,我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得到大学校方、同事和学生们的大力支持,现在身体也很健康。正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我的努力、规律的生活作息,我才能完成很多工作,并且希望做更多事情。当然,在私人层面,我也失去了很多——比如我的父母、我心爱的女儿、还有几段已经结束的关系。但我不会为这些事责怪任何人。我觉得我所爱的人,都是对我很好的人。我希望我为他们做得足够多。如今,我有很多朋友,有一个和我住在一起的好女婿,还有很多精彩的冒险之旅。(我刚刚结束了我人生中第一次阿拉斯加之旅,又看到了令人惊叹的鲸鱼!)我的生活真的很美好,我希望它能继续下去。
我现在的榜样是让·多洛雷斯·施密特修女(Sister Jean)。她上周刚刚庆祝自己的105岁生日,美国总统拜登还给她写了一封祝贺信,表达了对她的钦佩之情。让·多洛雷斯·施密特修女是芝加哥的一位罗马天主教修女,她也是洛约拉-芝加哥(Loyola-Chicago)男子篮球队的精神导师,这支球队是美国排名相当靠前的球队,足见作为精神导师的她身上的正能量是多么重要。她每次都坐着轮椅来到比赛现场,发表她对生活、快乐、能量和承诺的看法。年轻球员们都很喜欢她。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快乐,她的智力也没有随着变老受到影响。她曾说,长寿的秘诀在于爱他人,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并与年轻人多交流。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上一篇:没有了